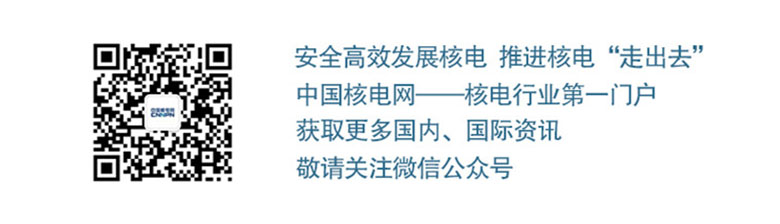2月17日,何梁何利基金2021和2022年度頒獎大會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其中,核工業功勛獎章獲得者,核武器工程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胡思得獲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據悉,由中核集團評選出的71位核工業功勛中,多人都曾獲得過何梁何利獎。其中,1994年,87歲的核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淦昌獲得第一屆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當時叫“優秀獎”)另外,我國第一任核潛艇總設計師、中國工程院院士彭士祿曾兩次獲何梁何利獎,一次是于1996年獲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另一次就是眾所周知的,于2017年獲得該獎科學與技術成就獎。

2013年,《中國核工業》雜志記錄并刊發了胡思得院士的口述,以下為摘編內容:
《見得•思得•值得》
我的名字
胡思得這個名字,是父親請一位老先生取的。先生說《論語》里寫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思得”二字由此而來。
然而我小的時候卻并不喜歡學習,很貪玩。記憶中最快樂的時光,就是和小朋友們在一起釣魚。3尺釣竿,一根絲線,大家盯著水面的浮標,很是無拘無束。那個時候,上課我不認真聽講,下課寫作業我也不用心,早上鄰居的小朋友已經開始晨讀了,我還在酣睡,所以成績總是很差。小學畢業時,全班有63個學生,我考第62名。
所幸,小學畢業后我進入到浙江省很有名的寧波私立效實中學,這所學校采取“寬進嚴出”的政策。初一時,我因考試不及格從秋季班留級到了春季班。直到1950年抗美援朝,學校里召集學生們報考軍事干校,我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報了名,不想卻因為體檢時說我鼻子有問題而落選。
這件事情讓我開始覺悟:參軍沒有指望了,以后想要為國家效勞,就得好好讀書,不能再這么玩兒下去了!到了初三的時候,我的成績開始好起來,趕在畢業前又從春季班跳級回到了最初的秋季班。
高一時一個偶然的機會,徹底改變了我學習成績。我們學校有位數學老師,叫蔡曾祜,號稱“蔡代數”。他因材施教,把全班同學分成3個小組。學習好的人放在1組,一般的放在2組,最差的放在3組,依照不同程度來安排各組的練習題目,而我就在第3組。奇怪的是,有一次數學考試,我得了全班第一名。我清楚地記得當時考了75分,而全班只有3位同學及格。蔡老師很生氣,上課時把大家訓了一頓,卻惟獨表揚了我。“你們看,第3組的胡思得這次考得最好。”蔡老師治學嚴謹,大家都很尊重他,他本身也很嚴厲,學生們都怕他,他輕易不表揚人,而我卻在班上第一次得到他的表揚。我心里暗自下決心,今后要拿出好成績,要對得起老師的表揚。其實,很多時候人是需要一點表揚的。
那之后,我對代數產生了興趣,成績很快就提高了,老師把我調到了1組。我做代數作業的時候,不僅把1組的題目做完,還主動把2組、3組的題目也做完,這些還不夠,我又拿來當時的《數學通報》做上面各種各樣的怪題,興趣越來越大,成績也越來越好,過了一年以后,我就成了數學課代表,同學們都稱我是蔡老師的得意門生。人一有興趣,勁就來了,勤奮就不會是一種負擔,而是一種享受。

胡思得(前排右一)在高中時期
我的大學
高考填報大學志愿時,我原本把數學作為第一志愿,但高考時幾何題沒做好,把數學成績拉下來了。但是物理成績卻考得很好,特別是最后一道題,許多同學都沒有做出來,而我做對了。也許是這個原因,我被錄取到物理系。時至今日再想,我覺得能與物理結緣,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
在復旦讀大學期間,對我人生最有意義的收獲就是學會了獨立思考。臨畢業前的那段時間,許多同學都去大煉鋼鐵。校領導考慮到學校要籌建核物理系(后稱物理二系),決定把理論物理專業的畢業班同學留在學校,籌建一個核物理實驗室,主要任務是設計實驗。我和小組同學一起去拜訪了盧鶴紱先生,請他指點。盧先生推薦我們做記錄宇宙射線粒子用的小氣泡室。
他說了基本原理,其余的要我們自己去摸索。經過短暫的調研,我們制定出了實驗方案。在蔡祖泉老師的安排下,有一位年輕的師傅,幫我們吹了許多玻璃的氣泡室。做實驗時需要有降壓、照相等一些關聯的動作,本來這些動作的配合要求是非常精細的,但當時簡陋的條件下,照了幾百張的照片,大都是空白,只有一次照到一張有很漂亮直線的照片。還有一張比較模糊,似有似無的樣子。這兩張照片給大家帶來不少快樂和鼓舞。
這件事培養了我獨立思考、敢于去闖的精神,改變了我曾經的學習態度和習慣。過去都是老師怎么說,學生就怎么做,先把條件都給你安排好了,叫你依樣畫葫蘆。而盧先生鼓勵大家獨立思考,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動手創造條件。
鄧稼先給了我一本全國唯一的書
大學畢業分配,我和其他5個同學一同被分配到二機部,當時我們連二機部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到了二機部后,正趕上第二天參加國慶游行,我就很開心地去了天安門,想看看毛主席長什么樣。游行回來后的半個月里,我們每天的任務就是看報紙。等其他學校的畢業生到齊后,宋任窮部長接見我們,跟我們說:“我是個穿軍裝的,搞技術要靠你們了。”
我還是不知道二機部是干什么的。在走廊里遇到一個從南京大學畢業的同學,問他,他也不知道,但他告訴我錢三強先生是我們的副部長,我們一想錢先生是研究核物理的,大概二機部跟核物理有關吧。
又過了幾天后,干部科的人帶我們三個畢業生去鄧稼先先生辦公室報到,辦公室里還有另外兩個人。鄧先生讓我們坐下后,就給了我們一本書讓我們讀,那是一本俄譯本庫浪特和弗里特里希合著的《超聲速流和沖擊波》。全國只有一本,聽說是錢三強先生從蘇聯帶回國的。
一本書,我們6個人都要看,于是大家就想辦法自己刻蠟紙復印,里面有些圖都是我們自己畫上去的。剛畢業的大學生外語水平普遍不高,大家就坐在一塊兒,將外文資料中的每一個生詞劃出來,分頭去查字典,再湊起來,琢磨全句的意思。就這樣日以繼夜地學,禮拜天也不休息。
過了好長時間,鄧先生什么都不讓我們干,只讓我們看書,我們還是不知道來二機部到底要干什么,有些同學開始鬧情緒了。后來鄧先生把我們幾個找來談話,說是我們國家要搞原子彈事業,但讓我們一定要保密,誰都不能說。當時聽了后,心里特別高興,也感到驕傲。
原子彈事業最初起步的那段日子,條件確實艱苦,但大家精神頭很足。到1960年、1961年,國家困難時期,很多人浮腫。當時的支部書記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到晚上10點把這些浮腫的病號趕回去休息。到12點鐘時,把所有人都趕出辦公室。但實際上呢,大家無論是病號也好還是一般同志也好,到外面轉一圈,等書記走了以后,又回來了。就這樣夜以繼日地干。
我還記得當時鄧先生住在北醫宿舍,他平日里騎自行車上下班,北醫宿舍到了晚上11點后就會拉起鐵絲網,我們幾個學生就一起送鄧先生,他先爬著翻過鐵絲網,我們幾個再把自行車給他遞過去。
說起鄧先生來,他留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平易近人。當時北京的冬天冷得不得了,手拿出來都凍僵了。到休息的時間,大家都到街對面的副食商店去烤火,那里生著爐子。有一次,忽然進來一個人,一看原來是鄧稼先。他是從國外回來的博士,是第一個分到我們單位里來的有高級職稱的專家。他的房間里也沒有暖氣和電爐,也凍得只好來烤火。我們想,這么大的專家都跟我們一塊兒烤火,那我們這點苦算什么?

三位院士與鄧稼先雕像合影,左一為胡思得
黃祖洽教我領悟專家的思維特點和學術技巧
對我而言,一畢業就被分配到二機部,在九院能有機會與錢三強、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朱光亞、程開甲、鄧稼先、陳能寬、于敏、周光召等一大批才華橫溢的科技精英在一起工作,接受他們的指導和幫助,是一件非常榮幸的事情。與這些大家在一起工作,我最能感受到的氛圍便是學術民主。
對于我們來講,研制原子彈這份事業是摸著石頭過河。蘇聯專家在的時候,曾給部、局領導進行科普,講解什么是原子彈,講過一個原子彈教學模型。我們要設計自己的原子彈不能照抄這個模型,因為用的核材料不一樣。但為了掌握設計技術,先得要算對這一教學模型。于是我們自己建立物理方程,尋找合適的物理參數和計算方法動手計算。
開始階段我們的計算結果與這一教學模型符合的很好,但算到一個關鍵位置時,發生很大的差異。為了尋找差異的原因,從各個領域調來的專家和我們這些大學生一起進行探討。每次探討,每個專家都從各自的角度提出看法和建議,有時候爭論的還很激烈,我感覺大家的智慧都是在這種激烈的爭論中給激發出來的。每次討論之后,根據大家提出的改進意見,啟動新一輪的計算。
記得原子彈內爆過程一共算了9次。剛開始,我們總是懷疑自己算錯了,不知有什么重要因素沒有認識到。但算了9次后結果基本是一致的,計算過程并沒有錯。那個時候計算機是手搖式的,很費時間,整個內爆過程算完一次需要2-4周。當時我們24小時三班倒,9次算下來共用了半年多時間。
到后來,周光召從國外回來參加我所工作,他很厲害,對手搖式計算機也熟悉,他親自演算一遍發現我們計算的結果沒有錯,那就要懷疑蘇聯專家的那個結果是錯的。這等于說一個沒有搞過原子彈的專家來否定蘇聯原子彈專家的數據,這談何容易呢!周光召從熱力學最大功原理出發,證明確實是蘇聯的數據不對。困擾我們的問題終于解決了。這件事情樹立了大家的信心,大家開始覺得我們是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原子彈搞出來的。
有一天晚上吃過飯,我和黃祖洽去散步,談起了這段日子專家們為一個計算結果反復討論的這件事。老黃語重心長地跟我說:參加討論會,不能光看熱鬧,不僅要注意每個人發言的內容,還得從他們的發言中悟出每個人的思維特點和學術技巧。你看,彭桓武先生有著名的3≈∞公式,即把兩個待考查因素的影響作比較,如果比值大于3,就暫不考慮分母的因素,把復雜問題大大簡化;程開甲和周光召則擅長用勒讓德函數展開和微擾法,取零級項、一級項、二級項來分解問題,分別列出方程求解,很快能給大家一些明確的概念和思路。而何祚庥呢,他卻能在激烈的爭論中,冷靜地思考各方的主要論點,去其偏頗,突出合理的內核,引導出一個更為完美的意見,他常常能取各家之精華,求同存異,做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小結,或提出下一步需深入思考的問題。老黃說你要特別細心去觀察、思考每一個人的特長,把這些本事都學到手了,日后你可就會成為了不起的科學家啦。

參加核試驗的理論家們
黃祖洽的這席話,對我觸動很大,尤其是我后來走上院領導崗位后,清醒地意識到領導從事核武器研究這樣集體性很強的科研群體,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去發現每個人的優點,然后安排工作。盡量讓他們在合適的場合、給合適的機會去充分施展他們自己的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
周光召教我要抓住理論與實驗結果不一致的地方
1962年,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方案已接近完成,所里成立一個專門小組負責聯系實驗。這個小組由鄧稼先和周光召親自指導。我被任命為這個組的組長。周光召比我年長六、七歲,更像我們的兄長。為了讓我們理論上有充分的武裝,老鄧和光召分別給我們組“吃小灶”,每星期給我們講兩、三次課。周光召講課從不用講稿,信手寫來,由近及遠,一氣呵成,令我贊嘆不已。
1963年開始,我們小組要去青海的實驗基地,臨別前周光召叮囑我:“一個有作為的科學家,不僅要重視理論,而且一定要重視實驗;理論和實驗結果一致當然值得高興;但有作為的科學家特別要抓住理論與實驗結果不一致的地方,因為從這種地方會發現理論或實驗的不足,有可能產生新的突破。” 周光召的話,我牢記在心,也使我受益匪淺。

胡思得(右1)陪周光召考察
從1963年起,將近4年多的時間我們都在實驗基地工作,使我有更多的機會深入實驗和生產現場,了解到許多第一手資料,接觸到很多實驗科學家、工藝專家和生產人員,聽到他們對理論方案的各種意見。我們在一起還常常共同設計實驗,有時我們還有機會親自動手安裝和計量實驗裝置。這些經歷對于大家豐富和完善原子彈的公差設計和聚焦理論方面有很大幫助,也對后來克服由于武器小型化帶來某一關鍵技術上出現的困難起了重要作用。
在此后的工作中,每當實驗結果出現與理論不一致的地方,我既不沮喪也絕不輕易放過,既思考理論上可能存在的毛病,也仔細推敲實驗數據的真偽和精度,努力尋找產生問題的原因。不僅要求這些原因能解釋當前的問題,而且還要與以前的結果相統一。每當我們揭開一個又一個的疑團,越來越多的現象為我們所探明和理解,心中那特殊的興奮和喜悅難以言表。

核試驗前,朱光亞對胡思得(右)面授機宜
回顧自己走過的這段人生經歷,我大學一畢業能分配到二機部九院參與我們國家核武器的研制,能為我國國防事業做一點事情、盡一點力,這一生不僅僅是無怨無悔,而且是非常值得和引以為豪的。

胡思得(左)與于敏(中)、胡仁宇重訪核試驗基地